行业新闻 
守护大足石刻的年轻人
早上8时30分,于利娟赶到大足汽车站,和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等待开往大足石刻游客中心的公共汽车。
这位生于1987年的姑娘是大足石刻的讲解员,和她一起乘车的,有为摩崖造像“治病”的修复师,有通过数字化手段复现大足石刻的工程师以及从事考古研究的学者……
宝顶山石刻是大足石刻的核心组成部分,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公元1174—1252年),现存造像近万尊。大足石刻是大足境内所有石刻造像的总称,这里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万余尊,规模巨大、题材丰富,至今仍是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公共汽车抵达游客中心后,车上的人们下车去往各自的工作岗位。近些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日复一日往返于石刻与住所之间。在守护千年石刻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将生活与石窟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融为一体。
“那段日子每天都过着一样的生活,没有提升空间,自己对未来也没有方向。”于利娟说。
那年,于利娟选择回到家乡大足。她偶然得知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现大足石刻研究院)正在招聘讲解员,考虑到“这里的人文和历史底蕴非常厚重,自己肯定能获得成长”,便努力入职于此。
“刚参加工作第一年,讲解词只能靠死记硬背,知识无法融会贯通。”于利娟回忆,“历史的,文化的,美术的,建筑的……大足石刻的知识根本学不完。”
为尽快适应工作节奏,于利娟白天听有丰富讲解经历的老师授课,晚上看书、整理自己的解说词,时常熬到凌晨才入睡。第二天清晨,她又早早起床复习,再到宝顶山石刻练习讲解。
王彦博是甘肃敦煌人,受敦煌文化熏陶,自幼便对文物、考古兴趣浓厚。从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专业毕业后,他便来到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
2024年5月,为确保大足区域内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大足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式启动。
从此,王彦博的微信朋友圈就变了风格:从记录吃喝玩乐的日常,变成了定格山川田野、高坡荆棘的野外工作日志。
王彦博同时期毕业的同学,大多进入了考古系统,散布在天南海北。由于工作性质和工作时间不同,老同学间的聊天逐渐变少,内容也从在校时的生活趣闻变成了一件件文物。

和王彦博一样,于利娟和更多选择扎根大足石刻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节奏早已被工作重塑。日复一日地“被时间撵着走”,他们却乐在其中,与时间赛跑,与大足石刻双向奔赴。
在担任讲解员的17年间,于利娟亲历了大足石刻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讲解方式从“靠嗓子吼”到“使用智能讲解器”的变迁,目睹了游客量的井喷式增长,见证了核心景区面积的一步步扩大……
但相比这些变化,更让她在意的是大足石刻本身说不尽的故事。“讲解工作没有尽头,会让你想要不停探索。”她说。
一次,于利娟带领游客参观大足石刻博物馆,一位游客对图片上的一块石碑提出疑问:“这块石碑上的字是谁雕刻的?”这个问题让于利娟一时语塞,对于这块石碑,她平时确实没有留意。
这件事情让于利娟意识到,讲解员的每句话都可能成为游客认识大足石刻的“一扇窗”,容不得半点含糊。
从那以后,《大足石刻铭文录》成了她的随身书,脚下“转山”,脑中“转”知识,确保每一句解说都有出处。
而当于利娟带游客“转山”时,另一群游客则在大足石刻数字展示中心的影院里欣赏8K球幕电影《大足石刻》。
“不仅如此,游客还能通过‘云游·大足石刻’线上平台沉浸式体验大足石刻。”大足石刻研究院文化创意和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肖人源说。
肖人源和同事的任务就是开展数字采集,对洞窟壁画和雕塑进行调研和测量,此后便可将大足石刻的影像以数字化的方式保存起来。
2018年,肖人源从重庆大学设计学专业毕业,听说大足石刻研究院在招人,便立马投了简历,那时他心里还在纳闷:“大足石刻招设计学的干嘛?不应该招考古学的吗?”
来到大足后,他才知道:自己成为大足石刻研究院文化传承与活化利用团队中的一员,更通俗地讲,就是做文创产球速体育Welcome品。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成员以“80后”“90后”为主。借助前辈的技术积淀和自身的创造力,他们已推出220余款文创产品。
“文创不仅仅是把石刻元素‘搬’到产品上。”肖人源说,“更多的是要在保留石刻神韵的同时,融入现代审美,我现在时常做梦都在忙设计。”
文物的最终结局可能是不断被消解,但大足的千年石刻却通过文字化、数字化、文创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不断获得新生。
6月20日上午,在大足石刻文物医院内,文物修复师蒋晓菁伏在案前眉头紧锁,正专注地修复一尊单体造像。
只见蒋晓菁左手持注射器,右手捏棉球,小心翼翼地在造像边缘轻轻“试探”,一点点加固石质本体。
文物修复师的技艺大多来自师传。蒋晓菁的技术,就师承于大足石刻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陈卉丽。
“陈老师接手的最大的工程就是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当时我也是修复团队的一员。”蒋晓菁回忆,“她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进行修复,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修复技巧。”
在长达8年的千手观音修复工程中,陈卉丽和团队成员每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面对冰冷的石壁,忍受着蚊虫的叮咬。

1952年,大足石刻保管所成立时,20岁的邓之金住进石刻旁的简陋工棚,一守就是半生;郭相颖老馆长在北山独居10年,夜夜与猫头鹰的叫声为伴,从看守者变成研究者;20世纪80年代,陈明光担任所长时,把文物创收的每一分钱都投入保护设施建设……
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战场,前辈们用青春抵抗岁月对大足石刻的侵蚀,现在的年轻人怀着同样的情怀,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人们与大足石刻的千年之约。
“文物保护者穷尽所能做的事就是与时间对抗、与毁灭抗争,让文物保存得久一些、再久一些。”陈卉丽说。
和前辈们相比,这些年轻人身上或许少了些时间的沉淀,但有更多元的性格、更丰富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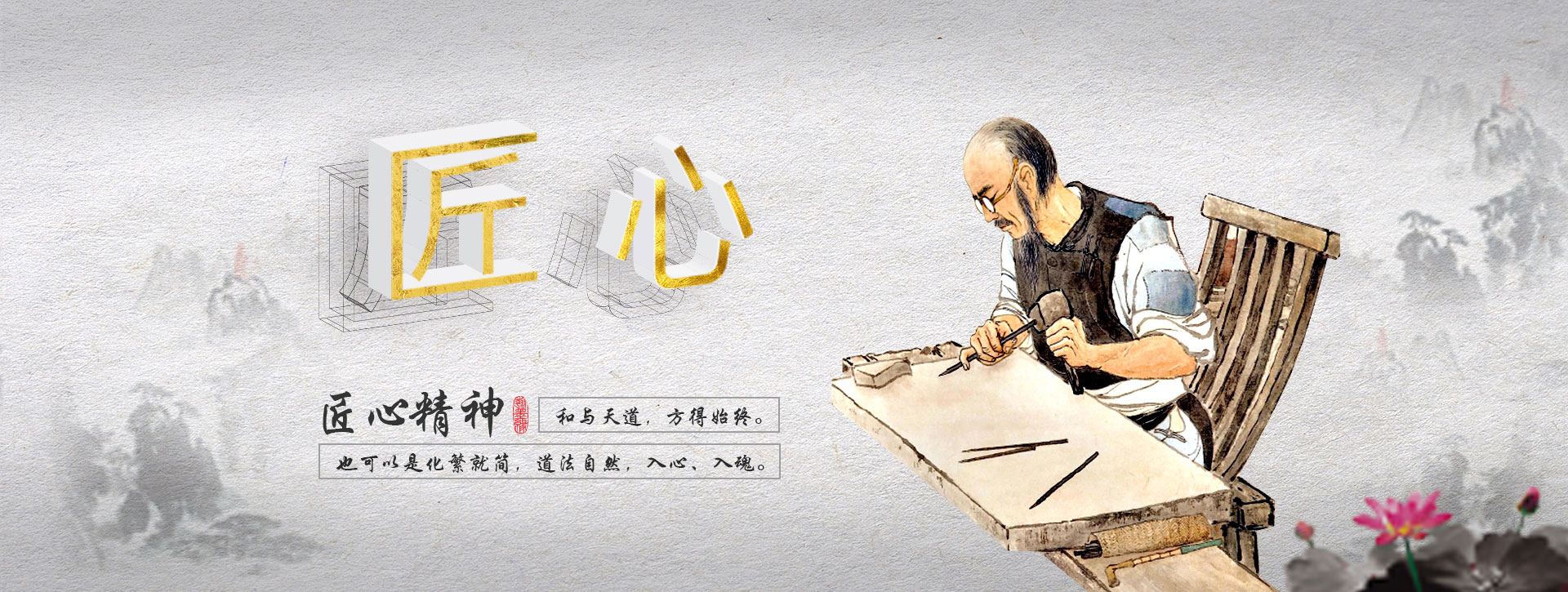

 2025-07-26 04:43:21
2025-07-26 04:43:21 浏览次数:
次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